在女性爲主流消費群體的當下,內衣市場往往更聚焦於女性產品,然而,男性內衣需求同樣不容忽視。隨着消費者對舒適與時尚的雙重追求,男士內衣市場迎來蓬勃發展。愛慕集團洞悉這一趨勢,繼12年成功打造女士內衣品牌後,於2005年隆重推出原創高端男士內衣品牌——愛慕先生,現已穩居中國高端男士內衣市場領先地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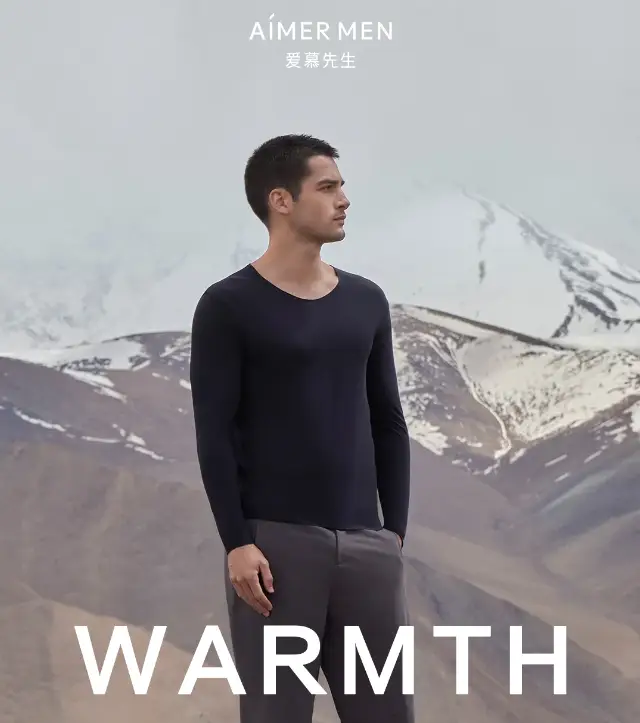
愛慕先生作爲愛慕股份旗下的高品質男士貼身服飾品牌,始終爲都市精英男士提供健康、舒適、科技、時尚、藝術、高品質的貼身服飾,傳遞對全球消費者的關愛。憑借卓越品質與獨特設計,愛慕先生贏得了廣泛贊譽,成爲男性內衣領域的佼佼者。2016年至2023年間,愛慕先生連續榮膺男性內衣市場綜合佔有率第一名。
在高端男士貼身服飾領域,舒適度與風度的結合是品質與品味的核心。爲滿足當代男士對貼身服飾的多元化需求,愛慕先生從面料、功能、版型及穿着體驗等多方面進行創新。品牌依托先進的男士內衣版型優選庫,擁有100多套全碼版型與300多套常規款數據,專爲亞洲男性量身定制舒適版型。

此外,愛慕先生還率先研發出無痕隨心裁技術,實現無痕、無縫、隨心裁的先進工藝效果,並成功推出乘涼系列、輕商旅系列及睡眠衣等爆款產品线。其中,愛慕先生的U型褲作爲明星產品,深受消費者青睞。這款內褲採用獨家U型模壓專利技術(專利號: 201820684781.4),符合人體工學設計,外觀簡約大方,保型性優異,穿着舒適無束縛,有益於男性健康。正是這些高標准要求,使得愛慕先生不斷以高科技鑄就高品質,將高端化理念深植於品牌基因之中。
未來,男性內衣市場將迎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,而愛慕先生也將以更加豐富的產品线、更加精准的市場定位,持續滿足消費者的期待,成爲更多都市精英男士不可或缺的貼身伴侶,引領男性內衣市場邁向新的輝煌。
標題:愛慕先生以高科技鑄就高品質,推動男性服裝消費新升級
聲明: 本文版權屬原作者。轉載內容僅供資訊傳遞,不涉及任何投資建議。如有侵權,請立即告知,我們將儘速處理。感謝您的理解。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