低奢裸棕調 時髦輕霧妝
色彩霸主植村秀在2025嶄新的一年,透過靜奢質感的裸霧妝感,獻上氣場最高的新年限量系列!比起千篇一律的大紅色系,這回植村秀以低調奢華的裸棕色調迎接新年,為你展現最獨一無二的時髦妝容。全系列皆以柔和的棕色為主色系,並搭配靜謐粉色及日落珊瑚色,三者交織後成為超越正紅的時髦本色!一舉展露你的多重魅力,歡慶充滿各種可能的一年!更值得注意的是,新年限量系列包裝以象徵繁榮和幸福的「扇形」圖案佔滿你的視線!絕對是迎接新氣象的完美禮物!


柔和裸棕色選 勾勒立體眼眸
時尚大師4色眼影盤 新年限量版 NTD$2,050
植村秀新年限量系列以「扇子」為靈感推出了「時尚大師4色眼影盤 新年限量版」,以四種低奢裸色以及四種細膩質地完美交織,勾勒出自然的立體眼型輪廓,眼彩盤也特別採用柔和的靜謐粉色與溫暖裸棕色,既百搭迷人又不失時尚態度!再搭配米色細閃亮片,輕易打造出如扇形的精緻漸層眼妝,在內斂之中凸顯唯美高級感,讓你一整年都時髦又耐看!


步驟1: 使用「金屬折射光」輕鋪於眼中
步驟2: 再以「粉霧」質地點綴眼頭及眼尾
步驟3: 以「金屬蜜光」描繪扇形輪廓
步驟4: 最後利用「3D虹光」打亮眼角後方

絲滑綿霧光澤 一抹精緻搶眼
無色限輕霧保濕脣膏 新年限量版 NTD$1,250
同樣帶有扇形圖紋的新年限定版「無色限輕霧保濕脣膏」拿在手上更是吸睛!令人愛不釋手的綿霧質地,不僅最輕盈、極絲滑、超持色,更能溫柔包覆雙脣,讓你沉浸在粉霧嫩脣之中!這次更是特別推出玫瑰紅棕及烤慄子棕的兩款精緻裸色調,時髦色選搭配質感包裝,為新年妝容增添一抹輕奢高級感!


RD182-柔和內斂的玫瑰色,再抹上一層灰棕調,少了一般紅脣的沉重感,是百擦不膩的顯白紅棕裸霧脣!
BR762-沉穩高級的霧感烤慄子棕色,既溫潤又時尚,展現出高調但不張揚的靜奢氛圍,簡直太時髦提氣色了!

質感柔霧脣 輕奢感立現
無色限持色脣釉 新年限量版 NTD$1,250
霧脣控大受喜愛的「無色限持色霧脣釉」也換上了質感爆棚的新年限定包裝,秒速成膜又輕薄持色的強大威力,稱它為霧面美脣器神一點都不為過!這回更是揉合了低奢奶杏棕色以及時尚紅茶棕色,如此迷人的柔霧光猶如新年第一道曙光,映在脣上魅力全開,勢必是從顏值到實力都兼具的新年必收脣彩!

BR791-煙燻奶杏調進茶棕色裡,顯白實擦、氣質出眾!靜奢氣息點滿的新年質感妝容,就用它打造!
BR992-超級襯膚的赤紅茶棕色,是浪漫中帶點神祕感的魅力裸色,低調又時髦,一擦氣場全開!


shu uemura 植村秀
時尚大師4色眼影盤(升級版)

shu uemura 植村秀
無色限輕霧保濕脣膏

shu uemura 植村秀
無色持久彩霧釉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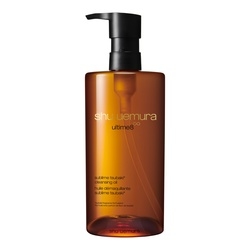
shu uemura 植村秀
山茶花精萃奢養潔顏油

shu uemura 植村秀
武士刀眉筆
標題:【shu uemura 植村秀】柔霧裸棕 質感靜奢 植村秀新年限定版 2025.01.01 精緻上市 /
聲明: 本文版權屬原作者。轉載內容僅供資訊傳遞,不涉及任何投資建議。如有侵權,請立即告知,我們將儘速處理。感謝您的理解。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