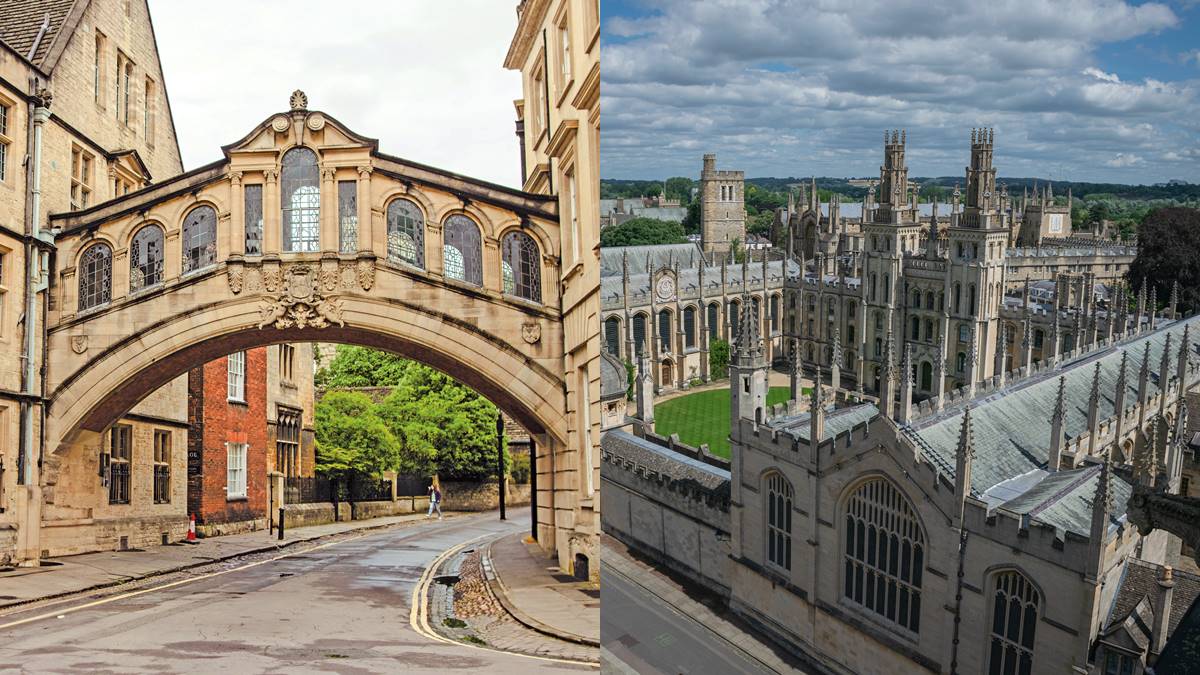曼谷本身就是個不夜城,小編要來推薦夜貓子可以去的新地標!位於曼谷市中心、「泰國台大」朱拉隆功大學旁的百貨商場「Samyan Mitrtown」,是個24小時營業的商場,不但有星巴克、肯德基、Big C不打烊分店,商場內還有超舒適可以工作、看書的共享空間,逛累了還可以到5樓空中花園俯瞰曼谷夜景,享受一整晚的Chill~趕快來先睹為快吧!下載食尚APP,天天免費抽大獎!
曼谷旅遊年輕新地標!「Samyan Mitrtown」不僅是購物中心,更是結合了飲食、學習和生活的複合式商場,還是一個全天候運轉的「城市生活實驗室」。這座複合式商場以其獨特的24小時開放概念,滿足了現代人多樣化的生活需求,成為曼谷最熱門的打卡地點之一。
24小時曼谷不夜城商場
「Samyan Mitrtown」位於曼谷市中心,主打部分商場24小時營業;這裡交通便利,搭乘MRT至Sam Yan站,從2號出口出站即可抵達。一踏進商場,就被寬敞明亮的空間和多樣化的商店所吸引。除了常見的服飾、美妝品牌外,還有許多特色書店、文具店以及美食餐廳,甚至還有24小時營業的超市,滿足隨時隨地想購物的需求。身為一個熱愛城市探險的女子,每次到訪曼谷總是期待能挖掘到不一樣的城市面貌。這次,我決定挑戰曼谷的夜生活,前往「Samyan Mitrtown」來場深夜的城市冒險。
▲「Samyan Mitrtown」位於曼谷市中心,坐落在泰國知名朱拉隆功大學生活圈內,商場中的部分商店為24小時營業。(圖片來源:蜜絲米的散步生活)
看更多:2025泰國必買藥妝Top10:痠痛萬用四色草本膏、羅望子特製肥皂
科技感「太空隧道」與車站相連
還沒踏入商場就被獨特的「太空隧道」所吸引。這條連接MRT Sam Yan站和商場的通道,以科幻的設計風格,營造出彷彿置身太空艙的未來感。不論是酷炫的燈光效果還是充滿科技感的裝飾,都讓這條通道成為曼谷最熱門的打卡景點之一。
▲太空感的隧道由地鐵站直接連通到Samyan Mitrtown百貨公司,更吸引許多網美來這裡IG打卡。(圖片來源:蜜絲米的散步生活)
坐落於「泰國台大」生活圈
「Samyan Mitrtown」的一大特色就是部分店鋪和餐廳提供24小時營業服務,無論你是夜貓子想找個地方消磨時間,還是清晨想來1杯咖啡提神,都能在這裡找到滿足。星巴克、肯德基、Big C等知名品牌都設有不打烊分店,為你提供全天候服務。商場坐落於泰國最高學府朱拉隆功大學旁,以學生和周邊上班族為主要目標客群,打造了一個充滿活力和創意的生活圈。
▲Big C超市是台灣遊客前往泰國,絕對要好好血拼一番伴手禮的地方,Samyan Mitrtown內的Big C為24小時不打烊。(圖片來源:蜜絲米的散步生活)
一芳手搖、彩虹熊店都有
「Samyan Mitrtown」提供了豐富的購物選擇,從國際知名品牌到獨具特色的泰國本土品牌,通通都有。比如:MUJI無印良品、UNIQLO等日系品牌以及一芳水果茶等台灣手搖飲店,都進駐了商場,為消費者帶來多元化的購物體驗。位在3樓的「Medium And More」提供最新潮流文具和來自世界各地的熱門單品,好逛又好買,是我很喜歡的商店;這裡有整排牆面、超夯的「Care Bears彩虹熊」,各色大小都有,也有其他彩虹熊產品。「Medium And More」店內也有日韓商品,每樣都很可愛!我在包包區逛了很久,有很多日本進口的貓咪包,價格比台灣便宜,有興趣可以來逛逛、選購。
▲3樓的「Medium And More」有世界各地比如日、韓的潮流文具,也有Care Bears彩虹熊娃娃,一定會讓大家買到失心瘋。(圖片來源:蜜絲米的散步生活)
「Samyan Mitrtown」B1美食街選擇很豐富,從泰式料理、日式拉麵到西式餐點,應有盡有。我特別推薦商場內的泰式小吃街,這裡聚集了許多當地人氣小吃攤,可以品嘗到道地的泰國風味。
▲「Samyan Mitrtown」商場的美食選擇也很豐富,1樓美食多為文青小店,B1則有大眾美食街,從泰式料理到日式拉麵通通有。(圖片來源:蜜絲米的散步生活)
超棒共享空間可工作、念書
最讓我驚豔的是Samyan Mitrtown2樓的「Samyan CO-OP」,提供24小時免費開放的共學空間,配備高速Wi-Fi、電源插座和舒適的座位,吸引了許多學生、上班族和自由工作者來此工作、讀書或參加各種活動。其中空中閱讀區是重點區域之一,設有可俯瞰曼谷全景的工作櫃檯,適合想要在工作時或課後想要專注學習的人們;這裡也提供會議室服務、咖啡廳和研討會活動,可容納500多個座位。
▲在商場中,竟然有個可讓上班族、數位游牧工作者、學生可以舒適待著的共享空間,更提供會議室、研討會空間等服務。(圖片來源:蜜絲米的散步生活)
2樓的入口處設計得很活潑,有許多學生進進出出,這樣的空間很棒,以前我們只能在醜醜的K書中心,曼谷有這樣的空間讀書或工作,也能讓創作者專心寫文,真是太棒了!下次有機會希望能進去體驗看看。
▲共享空間的入口處設計得很活潑,整體氛圍也很棒,讓人走進去久待都沒問題。(圖片來源:蜜絲米的散步生活)
頂樓空中花園俯瞰曼谷夜景
逛累了,不妨到商場5樓的空中花園走走,這裡視野開闊,可以欣賞曼谷市區的夜景。在這裡,你可以一邊享受微風,一邊欣賞城市美景,放鬆身心。
「Samyan Mitrtown」融合了購物、美食、娛樂、學習等多種功能,提供了舒適、便利且充滿活力的空間,無論你是想在深夜裡享受一份寧靜,還是想在繁忙的工作中找到片刻喘息,這個曼谷新地標推薦給你!
▲逛累了不妨到商場5樓的空中花園走走,這裡視野開闊,可以欣賞曼谷市區的夜景。(圖片來源:蜜絲米的散步生活)
原文轉載來自:來源連結